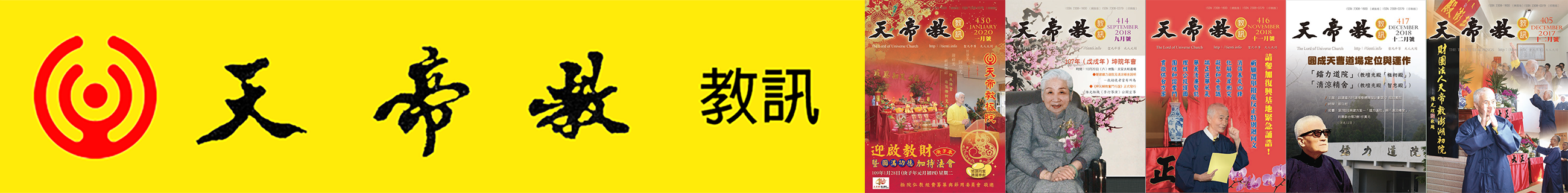小知大知境界不同 小年大年見識有差
趙光武開導師 2014-01-15 11:20
文/趙光武開導師
圖/編輯部
極院傳播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趙光武開導師,結合天帝教教義、昊天心法與丹經重新解讀《莊子》,拋磚引玉,期待激揚同奮解讀經典,與古聖先賢炁氣交流,為振興與發揚中華文化戮力以赴。天帝教《教訊》,自352期起連載。
「小大之辯」,是〈逍遙遊〉全篇的核心觀點。莊子不斷借物之大小,來比喻得道之人與世俗之人見識、境界的差異。當然,境界差異是很難描述的,我們平常說:「層次高」、「層次低」、「境界高」、「境界低」皆是比喻性說法,難免人言言殊。
前面談到「扶搖而上」的大鵬,或是下述「決起而飛」的蓬間小雀,雖然有著大小之分,但都有所依賴,有所期待,都無法真正的逍遙遊,進不了絕對自由的境界。
蜩與學鳩笑之曰:「我決起而飛,搶榆枋,時則不至,而控於地而已矣,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?」
莊子說:「蟬和斑鳩譏笑大鵬說:『我奮力飛起,遇到榆樹和檀樹就停下來,有時飛不到,只是滑翔落到地面而已,何必飛九萬里往南去呢?』」
莊子用「決」、「搶」、「控」,形容蟬和斑鳩的飛,很有意思,也顯示應用文字之妙。
因為「決」不是強調飛得快,而是瞬間衝出的動態。除了時間短促,就形象、意境來說,使人聯想到一股突破的爆發力,以及這股爆發力所轉達內心的得意。
「搶榆枋」的「搶」,有集、著、突三種注解。對應上一句的「決」,以「突」來解釋最恰當;「突」,是「撞」的意思。這樣理解「搶」字,蜩與斑鳩飛上榆枋樹時,急促而又勉強,且力有未逮的樣子便突顯眼前。
「控於地」的「控」,有操縱的意思,可以想像是適時、合度落在地上,好像穩穩妥妥,卻也透出內心的緊張,畢竟不穩當、有危險,才需要「控」。
蜩與斑鳩的「決起而飛」,就像蓄積力量突然爆發,嘣!跳過去,形容飛的距離有限。大鵬是「怒而飛」,飛得很高、很遠,這之間何止天壤之別。
小鳥小蟲自己也很得意,「搶榆枋」從這棵小樹飛撞到那叢草上,以牠們的體型來說,算夠遠了,也很痛快!時間、能力不夠,萬一飛不到掉下來怎麼辦?不過是掉在地上,又不會摔死。
適莽蒼者,三飡而反,腹猶果然;適百里者宿舂糧;適千里者三月聚糧;之二蟲又何知?
莊子說:「外出郊遊,路上吃三頓飯,回到家肚子還很飽;到百里以外的地方去,就要隔夜搗米準備路上吃的乾糧;到千里以外的地方去,那可得花三個月的時間來積聚糧食;這兩隻小動物又知道什麼?」
莊子在此提出行遠與積糧的關係,當然是有用意的;用意不是要說什麼適性自然,而是講人生的境界。前途遠大的人,就要有遠大的計劃;眼光短淺,只看現實的人,他抓住今天、明天就好了,不曉得有後天;另有一種人今天、明天、後天都不要,他要永遠。
本師世尊於民國76年正宗靜坐班先修第4期,主講「靜坐的目的」說:「我們要知道天上、人間的價值標準不同,人間是財富第一;人間社會一切都講財富,不管什麼東西都可以變錢的,黃金、美鈔、房地產、金銀、珠寶都是財富,稀少的東西。
這個觀念根本是錯的,我們人間社會以財富為標準、為價值觀念,價值最高的就是財富。這財富屬於我們專有的,屬於我的時間很短幾十年;幾十年我身體不存在,這財富有什麼用啊!要到另外一個空間去。另外一個空間,有它的生活空間、有它的生存條件、有它的價值標準。
另外一個世界,它的價值標準就是『功德第一』,看你在人間社會做過多少好事,幫過多少人,救過多少人,這是無形的精神價值標準。
所以我們要培養『精神價值標準』,不是『物質價值標準』;『物質價值標準』沒有方法可以衡量的,『精神價值標準』才是永久存在的。」
同時,本師世尊希望:「同奮要把眼光放遠,不要爭今天一時之名位,要爭千秋萬世之名位。同奮之使命為救天下蒼生,肯犧牲奉獻,即能達成使命,便可名揚四海,永垂後世。」(《涵靜老人言論集一》P.32)
本師世尊對同奮的期待就是永生,永遠的「精神價值標準」。
莊子提出行遠與積糧的關係,除了講人生的境界,更是要引出後文。
小知不及大知,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?朝菌不知晦朔,蟪蛄不知春秋,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靈者,以五百歲為春,五百歲為秋;上古有大椿者,以八千歲為春,八千歲為秋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,眾人匹之,不亦悲乎!
莊子說:「小智比不上大智,壽命短比不上壽命長的。如何知道是這樣呢?朝菌白天就死不知道有夜晚,寒蟬春生夏死、夏生秋死,不知道有春秋季節,這就是小年。
楚國南方有一隻靈龜,以五百年為一春季,五百年為一秋季;上古時代有一顆大椿樹,以八千年為一春季,八千年為一秋季,這就是大年。而彭祖到現在仍以長壽聞名,眾人都想跟他比,豈不是悲哀嘛!」
「小知不及大知」,是對前面一段描述的概括;「小年不及大年」,則引出後面幾段例證。第一個例證是「朝菌不知晦朔,蟪蛄不知春秋」,兩句都有個「知」,這個「知」並非指知識,而是對生命價值、生命潛質、生命境界的「知」。
「小知」亦可喻為生命不自由狀態;而「小年」則可謂生命不永恆狀態;對修道、學道的人來說,「大知」與「大年」可喻為得道境界。
智能深淺,壽命長短,小和大的境界比較,差別太大。每一個人都根據自己的生活歷練、思想見解、智慧等,對事物的識見、觀念多不相同。歷盡滄桑的老人,與剛出校園的草莓族,經歷人世間的經驗差別很大,難免對很多事物的見解不同,因此就有所比較。
氣候、空間、時間與顏色,因人的感受各異,人言言殊,譬如熱到什麼程度?每個人的感受不一樣。因此,一切都是比較的,不是絕對的真知識。
在《智忠夫人的一生》中,坤元輔教憶及:「蕭師尊不太傳授『靜坐』,除在山東會館開導師訓練班,為同道點道,會坐之外,他老人家因人而施教,擇人而傳授,因為他老人家認為每個人根器不同,因此,並不一定每個人都可以『靜坐』修性。
但,他老人家先要求他的學生,先做慎獨的工夫,就是先做好反省懺悔的工夫。他認為:一個人做好反省懺悔的工夫,就不會『入魔』。許多入定參禪的人,不入定還好,一入定馬上見神見鬼的『入魔』。百病叢生,而自己不知懺悔,反而說『道』不好!
蕭師尊他的經驗談,認為許多人本身罪孽深重,既不知培功立德,又不知反省懺悔,教他們『靜坐』入道,反而害了他們。」
本師世尊為了挽救三期末劫,大開方便之門,傳授昊天心法急頓法門,點道開天門,讓同奮直修煉神還虛,讓原人與原靈合靈合體,方便修煉元神;元神修煉好的人,才能修煉封靈。
但本師世尊從來不說靜坐的境界,因各人智慧有差,根器不同,業力不同,發生在身上的現象不盡相同,說多了,容易使人「著相」,不如不說。因此,本師世尊要求同奮只要「坐下去……」;他老人家教誨,一坐有一坐的功夫,一坐有一坐的境界,如人飲水,到什麼境界自己最清楚!這才是真知。
本師世尊首任首席使者在93年6月23日諭示:「宗教啟迪人心,具有創造文化之作用,惟以人心人性之根器相異,潛移默化之機緣亦不同, 天帝真道乃以『有教無類,一視平等』之精神而教,此為宗教之救贖行為,更是宗教信徒間相互相親相和之基石,遂行教化人心、啟迪人性之功能。」
所以,從上述莊子以大海作比喻,水不深不能載船,水要深,面積要夠寬廣,才能行駛大船;然後講大鵬鳥向南飛的時候,必須等待大風,大風揚起,才能超越九萬里的高空。
莊子以大鵬的高飛遠徙為自由樂境,為達到這一自由樂境,需要作準備,不是一蹴而就,隨心所欲的,將話題從得道之樂,引到修道上。
說出「負大翼,需風厚」,接著說「出遠門要準備相應乾糧」的譬喻;雖然沒明說修道的四大條件「財、侶、法、地」,但方便說法,點出根器不同,業力不同,智慧有差,這不正是功夫嗎?